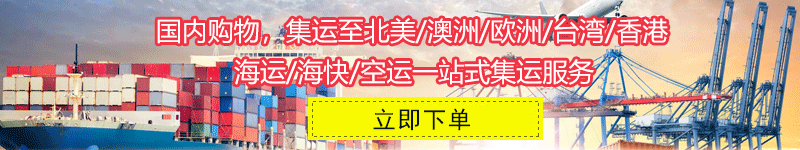第一部分:M1M2,社融,剪刀差
简单理解,M2是包含纸钞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在内的货币,而M1就是把定期存款去掉之后的M2。两者的差别主要就在于是否包含定期存款。通常所说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指M2。货币投放的渠道有两个,一是外汇占款投放,二是通过银行信贷投放。2014年以前以外汇占款投放为主,因为中国经济以出口驱动,产生大量出口顺差。2014年以后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央行创设多种结构性货币投放工具(可确保资金定向投放)。它们的投放增长越快M2的增速越大。
近年来央行创设多种货币投放工具:
分析M1和M2的增速,不是简单的数学比较,信贷会派生存款,会导致M1和M2的总量增加。剪刀差观察的是趋势,将M2的增长率和M1的增长率进行对比,M2增速-M1增速的剪刀差越大,货币存款活期化倾向越低,存款定期化比重较高,经济活力越低。M2与M1增速之间的剪刀差,可以用作判断资金活跃程度尤其是企业层面的观察变量。简单理解,M2-M1的剪刀差越大,意味着“死钱”越多。这通常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倾向于保守的投资决策,也就是很多钱暂时用不到,不会去投资、扩张产能,那就去存个定期吃利息吧。
M2比M1多了定期类存款。M2增速越快,“死钱”增速越快。M2-M1剪刀差扩大,说明“死钱”增加越快,经济向差,活力降低。M2-M1剪刀差收窄,说明“死钱”增加越慢,经济向好,活力增加。
举例:2023年12月M2-M1剪刀差收窄,经济活力有恢复趋势。
第二部分:货币信用组合
宽/紧和货币/信用,产生了4种组合。货币政策,指标:M2。信用,指标:社融。货币对应着资金供给意愿,信用对应着社会融资需求。利率对应着资金价格。显然目前(2024年1季度)是宽货币+紧信用的时期,M2增速不小,利率也低,但是社融始终萎靡不振,说明社会融资需求低,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当经济下行的时候,货币当局的目标是宽货币加宽信用,也就是货币政策是宽松的,但货币政策的效果依赖于社会杠杆主体和商业银行行为特征。由于信用派生状况依赖于社会杠杆主体和商业银行的行为,所以有时不能产生宽信用的实际效果。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希望导致宽信用的结果,宽信用是政策的一种结果,如果出现宽信用,那么也必然对应宽货币,因为货币是信用创造的。反之,从抑制通胀的角度,偏紧的货币政策是希望出现紧的信用,但紧信用出现,那么紧货币也会出现。
以信用松紧为分界点可以很好的描述股票市场的方向变化。具体来看,当信用宽松时,股票市场大概率处于牛市当中,即使是震荡市最终的收益也显著为正;但当信用开始紧缩时,股票市场几乎处于熊市当中,仅有2014年8月-2016年6月例外(配资与杠杆掀起的牛市,在M2和社融数据中很难体现)。若以货币政策松紧为分界点,股票市场的表现并不喜人,因而,市场信用状况的变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更大。
对于社融,还要观察结构,从而判断社融质量。2023年2月社融数据,政府债替代企业债加杠杆,但钱不知其所往。
首先,如果合并计算政府债和企业债的整体增速的话,总量同比增长11.6%,是个相当不错的数据。
其实相比于总量百亿、合计占总社融比重仅26.5%的债券,市场更关心社融占比长期维持60%左右的信贷数据。但是随着名义上的小微贷和消费贷陆续变为实际的存量房贷置换和场外配资等各种“套利”操作,信贷结构数据已经水到难以分析。总量数据又长期维持不变,难以得出什么有效结论。
反而是近三年来政府债和企业债的此消彼长更具备分析价值。同比2023年的春节月,政府债的实际增速高达16.65%,企业债则是1.64%,聊胜于无。从总量来说,过去一年里,政府债余额增加了10万亿,企业债几乎持平。
当然,如果政府加的杠杆同样可以顺利转化为投资、采购的话,那么结构上孰进孰退并没有大影响,经济同样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扩张,进而体现为GDP的增长、通胀的回升、居民收支的扩张、企业利润的增长、股市的上涨。然而现实中,M1并未像政府债一样高速增长,却和企业债的变动趋势更接近,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M2及政府债截然不同。
尽管社融总体增速看起来仍可圈可点,但结构上主要是政府在加杠杆,市场化的主体实质上是在去杠杆的;而政府加上去的杠杆转化为“实物工作量”的效率却远不及市场主体。
我们为什么关心社融?因为社融的概念是“实体从金融体系中融到了多少钱”。实体为什么要融资?为了融到手里再存到银行定期里吃利息吗?当然不是,正常的逻辑下,实体融到了钱就要用出去,企业去投资设备厂房、采购原材料、雇人搞生产;居民买房、买车、买家具电器,这些钱,都应该呈现为M1的增长。
然而2018年之后,M1增速就和社融增速渐行渐远,仅在2020年有过一段趋势性的回归,随后便再次远离。
在过去两年,不管是以辜朝明为代表的日式经济理论学者,还是传统马恩理论学者都建议政府加杠杆来承接企业端的熄火期扛起经济增长的大旗。政府加没加杠杆呢?当然是加了,加的很猛。
至于经济呢,你要说它增长了吧,那确实也是5.2%的增速,相当威猛,但还是感觉哪里不太对。就是,明明政府加了这么多杠杆,但是却没在市场中看到这部分钱。钱去哪儿了呢?
从好的角度猜测,也许还在国库里积而未发,或者是置换了一部分政府隐债(隐债指的是除了城投表内债以外的部分,比如拖欠工程款、工资、承诺补贴以及“白条”之类的债务。因为城投的表内债是明的,能看到总量是持平而非收缩,所以如果政府债冲销了什么东西,那应该是表内看不到的那部分债务)。
如果是前面两者,意味着钱早晚能花出去,或者等隐债冲销完了,就可以再次开始扩张了。但如果不是前两者,而是再次直接回流到了金融体系里,那就意味着信用扩张的完全失效,和总量、增速都没有关系了,是市场配置的失灵。
第三部分:股市表现实证分析
举例1:2018年紧货币,M2增速从年初9%跌到8%左右;紧信用,社融增速从12.7%跌到9.8%。股市跌满1年。
举例2:2020年宽货币,M2增速从年初8%升到11%左右;宽信用,社融增速从10.7%升到13.3%。社融升速最快的4月-10月也是股市涨幅最快的阶段。
举例3:2023年紧信用,社融增速在9-10%之间徘徊,比2018年最低9.8%更低。央行没有主动紧货币,但社融降速,派生货币的也被动降速,被动造成紧货币状态。M2增速从年初近13%降到10%以下。股市从2月开始跌满1年。
第四部分:根据货币信用周期配置资产